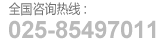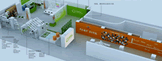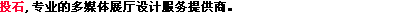章剑华新书介绍画作故事《AI:现代苏州繁华图》
文章来源:章剑华长篇纪实文学
《经典之城——苏州人文经济发展三部曲》

乙巳开春,DS横空出世,AI席卷神州。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引发了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场巨变。无疑,AI也将深刻影响文学艺术包括绘画艺术创作的变革与创新。
许多书画家对AI高度关注,并尝试运用AI工具进行书画创作。徐惠泉也是AI的热情拥抱者。
徐惠泉,生于1961年,苏州人。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第九届理事,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美协副主席江苏省美术馆名誉馆长,南京市文联副主席,南京市美协主席,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作品入选第八、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届全国美展,获第二届“枫叶奖”国际水墨画创作大赛金奖, 第四届全国工笔画展铜奖等。代表作品收入《中国当代美术全集》《中国现代人物画全集》《中国工笔画全集》《20世纪中国绘画》等重要合集;作品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专业机构收藏,已出版个人专著画集20余部。
徐惠泉作为苏州本土艺术家,其作品常以江南美学为基调,注重写意精神与技法的结合。多年前,徐惠泉与苏州几位画家创作了题为《苏州繁华》的国画长卷作品。

这是一幅以苏州城市风貌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展现了苏州的独特文化底蕴和繁华景象。这幅作品融合了徐惠泉在水墨重彩人物画方面的深厚造诣,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将苏州的古典美与现代气息完美结合, 不仅描绘了苏州的城市景观,还通过人物的刻画传递了苏州人的生活情趣和文化内涵,展现了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魅力,体现了徐惠泉对苏州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艺术表达,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充满诗意的苏州画卷。
DS(DeepSeek)爆火之后,徐惠泉十分关注,并产生了与AI合作创作一幅《新苏州繁华图》的想法。经人介绍,他结识了AI专家孙峰峰,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进行合作与尝试。
孙峰峰,南京投石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南京投石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他围绕艺术与科技的方法论、AIGC赋能的沉浸式交互艺术展、装置艺术作品的创意设计等,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研究和应用性实验,在数字媒体艺术和人工智能艺术创作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显著的成就。
著名画家与AI专家合作,实乃强强联手,实现了艺术与科技的融合, 碰撞出绚烂的艺术火花。他们很快达成了这样的创作目标:
山水写意融数字,丹青妙笔焕新城。

其创作思路是,运用AI绘画大模型技术,以吴门画派沈周、文徵明、 唐寅、仇英和黄公望、王希孟的笔墨意蕴为艺术基底,以苏州当代城市风貌为骨,通过AI技术重构传统山水画的空间叙事逻辑,绘制长卷《新苏州繁华图》,呈现出一座兼具水墨诗意与科技质感的“现代姑苏”。
他们在一起反复探讨,明确了长卷的主题、内容和形式:
一是自然与人文交织。保留太湖烟波、姑苏遗痕、虎丘斜塔等传统意象,融入金鸡湖摩天轮、东方之门、苏州中心等现代地标。
二是时空维度的叙事。长卷的“远处”以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为蓝本,以吴门画派的笔法,主要呈现老苏州的古风今韵;长卷的“近处”和中心位置,以徐惠泉的笔法,主要呈现新苏州的现代气象。
三是AI艺术符号的呈现。基于深度学习和概率扩散模型的高级图像处理技术形成的投石气韵再生AI绘画生成算法,通过收集多位画家的众多画作,对图片打标签,训练LORA模型等工作流程,不断地投喂、训练,让AI系统习得了画家们独特的气韵和画风精髓,不仅能够模仿传统绘画的风格,还能够在长卷中创造出新的艺术符号,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现代科技感。
四是长卷高0.68米、长18米,以现代新城为主体,强化现代人文色彩。
这一构思确定后,徐惠泉与孙峰峰分别行动,各自开展工作。

徐惠泉亲自动手,绘制了长卷的示意图,确定了基本的布局、内容与形式,并与苏州籍画家、摄影师姚永强一起,搜集有关文字资料、照片和画册,交给了孙峰峰。
孙峰峰团队则按照徐惠泉的构思和示意图,设定了这样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
先是古画学习。AI系统深度学习吴门画派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和黄公望、王希孟的笔触、构图、墨色层次,提取“披麻皴”“浅绛设色” 等风格特征。
再是实景建模。优化AI算法,解决传统山水透视与现代建筑结构的兼容性问题,并通过3D扫描获取苏州地标建筑及街景数据,构建数字孪生城市模型。
接着是人机协同创作。AI生成的水墨长卷由徐惠泉其进行美学修正,强化留白意境、虚实对比,增添部分内容和细节,如现代建筑、人文景观等,并进行适当的补笔与着色,确保整体气韵贯通。最后完成题跋、印章的数字生成与布局设计,输出高精度数字长卷及宣纸微喷实体卷轴。
这幅由徐惠泉和孙峰峰团队合作完成的AI作品,表面上延续了传统水墨长卷的形式美学,内里却蕴含着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文化革新。当水墨的氤氲墨色遇上算法的精确计算,当艺术家的主观表达融合机器的生成能力, 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一件新作品的诞生,更是一种艺术范式的根本性转变--从“人类独白”到“人机对话”的美学新时代正在到来。
《新苏州繁华图》解构了传统水墨艺术的创作神话。在传统认知中,水墨画是艺术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纯粹精神产物,毛笔与宣纸的每次接触都被视不可复制的灵感瞬间。而徐惠泉和孙峰峰却大胆地将AI 引入这一神圣领域,让算法参与构图、笔墨甚至意境的生成。这种创作方式,彻底动摇了艺术原创性的传统定义——当一幅水墨画的部分元素源于深度学习对历代名作的解析与重组时,“独创性”不再意味着无中生有,而表现为对文化基因的智能筛选与创造性转化。作品中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山水楼阁,恰如文化记忆的数字幽灵,在人与机器的协作中获得了新生。

在形式语言层面,这件作品创造了独特的“数字水墨语法”。AI系统通过分析大量古典水墨作品,掌握了皴法的节奏、留白的哲学与构图的法则,却不受物理笔墨的限制。由此产生的线条既有宋代山水的严谨骨法, 又具备数字时代特有的流畅与精确;墨色渲染既保持传统“五墨六彩”的层次感,又增添了算法生成的微妙渐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长卷中现代苏州元素的融入——东方之门、苏州中心等地标建筑与传统园林和谐共存, 这种时空拼贴并非简单的并置,而是通过 AI的风格迁移技术实现了视觉语言的统一。作品证明,数字技术非但没有消解水墨的精神内核,反而为其表达开辟了新维度。
《新苏州繁华图》的创作过程本身即一场精妙的“人机共舞”。与常见的“艺术家主导AI执行”的模式不同,徐惠泉和孙峰峰与AI系统建立了真正的对话关系。AI生成的数百幅草图成为艺术家的灵感来源,而艺术家的选择与修改又反过来训练AI更好地理解创作意图。这种互动打破了单向度的工具主义技术观,呈现出主体间性的新型创作关系。当艺术家开始欣赏算法出人意料的构图建议,当AI逐渐掌握艺术家的审美偏好,创作行为便升华为两种智能形态的创造性碰撞。这一过程暗示着,未来艺术的创新可能不再源于人类天才的孤军奋战,而来自生物智能与人工智慧的共振。
《新苏州繁华图》的展出方式同样值得玩味。数字长卷既可以作为整体展示,也能分解为多个片段独立呈现,观众还可以通过交互设备探索画面细节或查看创作过程。这种可变性彻底颠覆了传统长卷“移步换景”的线性观赏模式,代之以非线性、可扩展的数字体验。水墨艺术首次真正获得了“超文本”特性一-每一处笔墨都可能链接到艺术史参照、创作数据或城市记忆。艺术品的边界由此变得模糊而开放,它不再是一个完成的对象, 而成为不断生成的意义网络。
当然,这种人机合作模式也带来了深层焦虑:当AI越来越深入地参与艺术创作,人类艺术家的角色将如何重新定义?《新苏州繁华图》给出的启示是,未来的艺术家或许不再主要是技术执行者,而将成为“意义策展人”。他们的核心能力在于设定创作框架、引导AI探索方向,并在算法输出中进行文化判断与选择。徐惠泉和孙峰峰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正是如此: 他们不再追求对笔墨的绝对控制,而是专注于整体构思与审美把控,将部分执行权交给AI。这种分工变化不是艺术家权力的削弱,而是其职责的升华。
《新苏州繁华图》所预示的艺术未来,既不是人类艺术的终结,也不是技术的全面胜利,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共生图景。在这里,水墨的“气韵生动”与算法的“深度学习”相互启发,艺术家的文化自觉与AI的计算能力彼此增强。这种合作不满足于表面上的形式创新,而是试图在方法论层面重新构想艺术的可能性。
假如沈周、文微明、唐寅、仇英、黄公望和徐扬看到这幅《新苏州繁华图》,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呢?这当然不得而知。但今天的观众,站在18米的长卷前,他们看到的不仅是苏州的古今风貌,更是一幅人机关系的新地图——
在这里,创造力的疆界已被重新划定。而艺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见证着苏州的历史变迁和艺术的新的可能性。